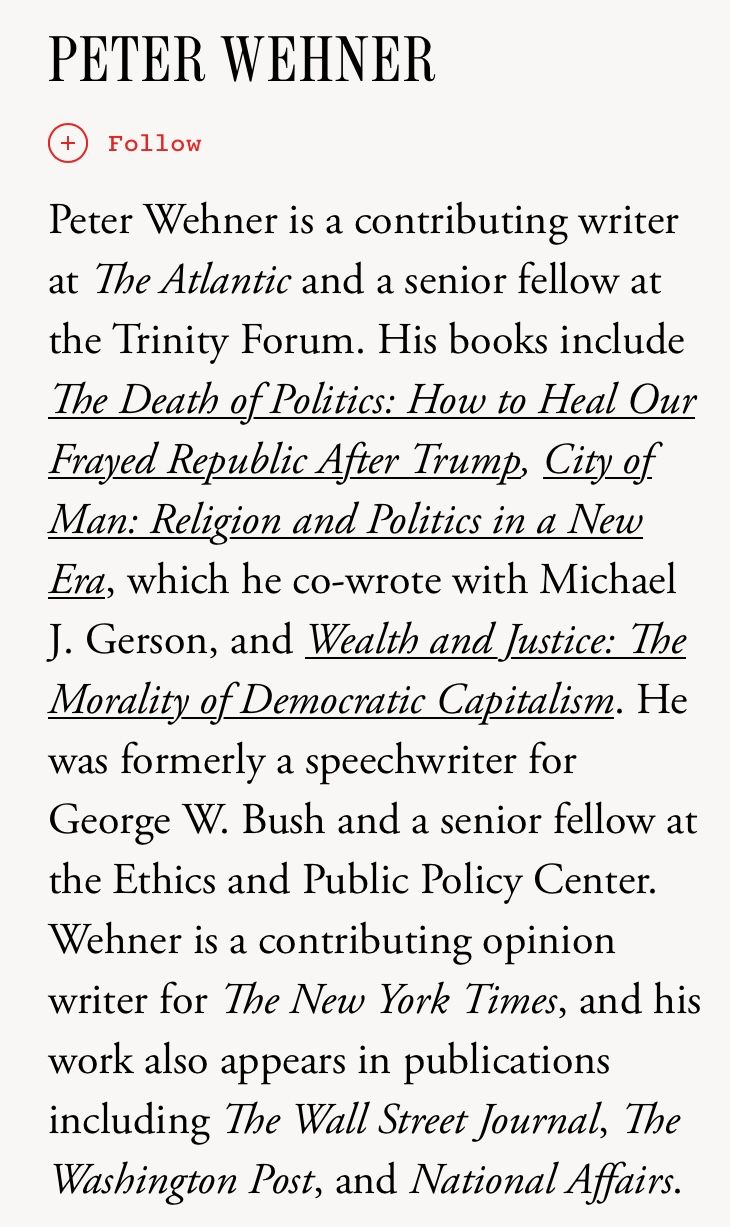《大西洋月刊》:从放弃PEPFAR看美国福音派的真实信仰
-
《大西洋月刊》:从放弃PEPFAR看美国福音派的真实信仰
一个经常在公共场合发表立场的主流宗教运动,在川普大幅削减非洲抗击艾滋病计划后,却异常沉默。
**作者:彼得·韦纳(Peter Wehner,福音派基督徒。他曾担任三届共和党美国总统的演讲撰稿人。他是三一论坛的高级研究员。韦纳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也是《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并著有《政治的死亡》。)
日期:2025年7月6日**
编译:临风

Why Evangelicals Turned Their Back on PEPFAR
A religious movement that has so often taken public stands has been unusually quiet since Trump gutted the program to combat AIDS in Africa.
The Atlantic (www.theatlantic.com)
2006年,时任美国全球艾滋病协调员的马克·迪布尔(Mark Dybul)大使访问了埃塞俄比亚一家由“仁爱修女会”(Daughters of Charity)经营的孤儿院。这里是400多名HIV阳性婴儿和幼儿的避难所,他们被发现于垃圾堆、路边或孤儿院门口。当迪布尔与时任总统小布什高级政策顾问迈克尔·杰尔森(Michael Gerson)穿过这座庞大院落时,来到餐厅,看到一幅耶稣被一群儿童环绕的壁画。修女们告诉他们,这幅壁画描绘了在孤儿院因艾滋病去世的孩子们的肖像,孩子们会来到这里与墙上的“朋友”交谈和玩耍。
疫情绝非仅限于埃塞俄比亚。它正在肆虐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全球40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有三分之二生活在该地区。超过1200万儿童因艾滋病成为孤儿。
“我们确实正面临国家级危机,”博茨瓦纳(Botswana)总统费斯图斯·莫加伊(Festus Mogae)于2000年表示,“我们面临灭绝威胁。死亡人数令人震惊。我们正在失去最优秀的年轻人。这是一场空前危机。”
在博茨瓦纳的部分地区,75%的孕妇感染了HIV。大多数疾病会夺走老年人或婴儿的生命,可是,迪布尔于2018年回忆道:“但这种疾病却在夺走社会中最富有生产力和繁殖能力的群体。因此,不仅许多家庭由孤儿抚养,整个村庄都由孤儿管理,因为其他人已经去世。”
随后,PEPFAR计划出台。
“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 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于2003年由小布什总统首次授权,这是任何国家为应对单一疾病所作出的最大承诺。小布什总统表示,这是“超越当前所有国际努力的仁慈之举,旨在帮助非洲人民”。
PEPFAR获得两党强烈支持,被认为拯救了2600万人的生命,并使近800万婴儿得以在没有艾滋病的情况下出生。它彻底改变了艾滋病疫情的格局,并帮助稳定了非洲大陆。
PEPFAR不仅是迄今为止美国与非洲关系中最成功的政策,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外交政策项目之一”,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贝琳达·阿奇邦(Belinda Archibong)去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2006年访问埃塞俄比亚期间,迪布尔曾到访阿克苏姆(Axum)附近的一个农村村庄。“黎明时分,雾气笼罩着小镇,仿佛回到了几个世纪前,”迪布尔告诉我,“当地农民驾着驴车在街上穿行,教堂的尖顶从雾霭中若隐若现,钟声响起,召唤人们前往祈祷和集市。在当地诊所访问时,诊所主任——同时也是村长老者和社区领袖——多次提到PEPFAR。我问他PEPFAR是什么意思。他的回答让我震惊。“PEPFAR意味着美国人民关心我们。”
约翰·罗伯特·恩戈尔(John Robert Engole)于2004年来到乌干达坎帕拉郊区一家由信仰组织“Reach Out Mbuya”运营的诊所。这是一家由宗教信仰驱动的非政府组织(NGO)。当时他身体非常虚弱,患有严重的结核病,免疫系统几近崩溃,正处于艾滋病晚期。但正如埃丝特·纳卡齐(Esther Nakkazi)在《哈佛公共卫生》(Harvard Public Health)中所写,恩戈尔成为了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治疗的首位受益者。“PEPFAR开始之后,死亡停止了,”玛格丽特·容克(Margrethe Juncker)告诉纳卡齐。容克是一位曾在乌干达照顾城市贫民区艾滋病患者的丹麦医生,也是恩戈尔的主治医生。她称该项目为“奇迹”。
之后,唐纳德·川普上台了。
川普改变了一切
川普在其第二个任期第一天签署了行政命令第14169号,要求暂停所有外国发展和援助项目90天,待进一步审查。随后发布的停工令冻结了已拨付的资金和正在进行的工作,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相关项目陷入停滞。该行政命令还解散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该机构是美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机构,也是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的主要实施机构。
暂停工作令最初冻结了所有PEPFAR项目和服务,暂停了实地工作,包括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提供。尽管PEPFAR(占联邦预算的0.08%,并一直被评估为高效且问责的项目)于2月获得有限的豁免,允许其继续提供“挽救生命的艾滋病服务”,但该豁免的实际实施却被推迟、碎片化且混乱。供应链中断;诊断和治疗服务也受到影响。大量员工被裁员。诊所被关闭。
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报告,“结果是前所未有的运营混乱、资金断裂、实施伙伴关系崩溃,以及在许多情况下诊所关闭”。 现场人员报告称,艾滋病服务普遍中断,PEPFAR受益者面临毁灭性后果;耗时数年建立的基础设施已被摧毁。即使川普政府明天重新启动PEPFAR,这一情况仍将持续。
目前估计,由于不到六个月前开始的PEPFAR实质性停摆,已有超过7.5万名成人和儿童死亡。每3分钟就有1名成人丧生;每31分钟就有1名儿童死亡。终止PEPFAR可能导致本十年末新增多达1100万例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和近300万例艾滋病相关死亡病例。

2025年2月12日,肯尼亚内罗毕的“尼亚姆巴尼儿童之家”(Nyumbani Children's Home)后方,儿童大小的墓碑上放置着十字架,这些墓碑是因艾滋病并发症去世的儿童的墓地。(托马斯·穆科亚/路透社)
一旦PEPFAR计划宣布,许多福音派团体和个人在支持该计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认为,他们的信仰呼召他们去关怀病患和贫困者,为受压迫者发声,并展现他们对生命神圣性的承诺。然而,随着这场人道主义灾难的不断升级,鲜有美国福音派牧师、教会、教派或非教会组织公开反对削减PEPFAR。据我所知,他们似乎也没有此类打算。
为何如此多福音派人士保持沉默?这主要是由于无知或冷漠?同情疲劳?还是对川普的忠诚?牧师们的沉默是否源于担心触怒会众?希望将事工与政治分离?还是其他事工承诺?我向超过二十位人士提出了这些问题,其中大多是现任或前任牧师,部分人同意公开发言,另一些则要求匿名以坦率表达。他们讲述的故事是复杂的。
几位受访者表示,大多数基督徒,尤其是牧师,根本不知道PEPFAR的存在。“它做了非凡的善事,却几乎不为人知,”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Knoxville)雪松泉长老会教堂(Cedar Springs Presbyterian Church)的詹姆斯·福赛思(James Forsyth)告诉我。
“这就是问题所在。想想在普通教会中沿着长椅走一圈,或在普通城镇的街道上走一走:我敢打赌,绝大多数人无法告诉你PEPFAR是什么,它取得了什么成就,它正面临威胁,以及为什么这很重要。”
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Alexandria)格罗维顿浸信会教堂(Groveton Baptist Church)的克里斯·戴维斯(Chris Davis)是PEPFAR的坚定支持者,他告诉我,对许多人来说,这个问题似乎很遥远。“很少有福音派信徒去过马拉维(Malawi)的‘棺材街’(Coffin Row),或认识去过那里的人,”他说。(在PEPFAR实施前,马拉维首都利隆圭的许多木匠转行制作棺材,沿肯雅塔大道的作坊因此获得了一个阴森的新名字。)
“因此,当这个问题没有直接影响你的朋友、邻居甚至大家族的成员,比如患癌症或2型糖尿病,它往往更具理论性而非个人性。”
许多教会确实是在关怀“最弱小者”,用耶稣的话来说,并将信仰与社会良知相结合。但他们在其他问题上这样做,而非PEPFAR。
华盛顿州贝尔维尤市(Bellevue)贝尔维尤长老会教堂(Bellevue Presbyterian Church)的斯科特·杜德利(Scott Dudley)认为,PEPFAR的毁灭是一场悲剧,但他的教会正忙于应对其他正在发生的变化。“我们没有关注PEPFAR的主要原因,”他告诉我,“是因为我们更关注难民、寻求庇护者和移民问题。
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合作伙伴是基督教非营利组织,它们在USAID预算削减中损失了巨额资金。”他指出,教友们有被压垮和耗尽精力的风险,因此他鼓励他们专注于自己已深度参与的领域。另一位参与教会事工的人士这样向我解释:“我们都是有限的生物,各自被召唤投身特定的事业。教会应该回应不公,但不可能随时随地回应所有不公。”
一些牧师则表示,他们对涉足政治持保留态度,尤其是可能引发教会内部矛盾的政治议题。许多基督徒认为,教会是敬拜的场所,而非制定政策或指导政策的机构,即使是涉及紧迫的人道主义问题亦是如此。
有人告诉我,牧师的责任是“在任何时候都宣讲上帝的道,并祈祷他的会众在基督里成长,足以在他们影响的领域改变世界。在极少数情况下——例如对另一个国家宣战——从讲坛上宣讲一个明确的政治议题可能是正确的。但总体而言,我认为这只会进一步分裂和削弱教会。”
有原则地避免将讲台政治化,有时很难与人类本能的恐惧区分开来——害怕在某些议题上发声会引发教众中川普支持者的愤怒反应。即便是那些出于道德良知,倾向于对PEPFAR被削弱公开发声的牧师,也往往会三思而后行,因为他们不愿成为自己教会成员攻击的目标。
一位偏保守立场的牧师向我坦言:“有时候我真希望我不是个牧师,这样我就能更大声、更清晰地发声了。”
美国长老会(PCA,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的一位牧师——该教派本身就偏保守——这样对我说:“有些牧师充当了‘守门人’,在社交媒体上花费大量时间公开羞辱那些在政治观点上与他们不同的人,施压他们作出回应,甚至要求他们辞职。”他担心这些攻击会使他偏离对本地教会的责任。“我不知道在这种高度极化的环境中发表公开声明能有什么作用,除了给我家人和教会带来痛苦,”他说。
他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感受的人。曾在弗吉尼亚州北部一间有影响力的福音派教会担任牧师的一位人士告诉我:“任何曾在争议性‘政治’议题上发声的牧师——无论那是不是道德问题——都知道自己会从一些会众那里收到极其愤怒的反馈。这会让他犹豫不决。他会想,自己是否真的能在小小的教会群体中起到正面影响。”(这位人士说,如果他现在还在担任牧师,他希望自己仍然会站出来发声,尽管可能会带着犹豫之心,因为“牧师也必须警告羊群周围的危险”。)
一些在基督教救援与发展领域工作的人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本届政府表现得反复无常、情绪易变。他们仍希望能改变政策方向,但也担心公开批评会让政府态度更为强硬。还有一些人指出,许多保守派教会对政府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福音派群体投向右翼政治以来,一位牧师告诉我,福音派人士几乎将里根1981年就职演说中的一句话奉为圭臬:“政府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他所在的教会支持医疗传教士和在海外开展健康工作的非营利组织,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支持PEPFAR。“教会普遍对政府项目抱有怀疑,认为凡是政府主导的东西都低效腐败,”他说。“所以政府项目被削减,通常并不会在福音派圈子里引起强烈抗议。”
一位曾参与牧会的人这样描述这种思维方式:“这不应该是政府来做的事。即使PEPFAR项目非常出色,挽救了数百万生命,美国政府也不应该动用通过强制征税获得的公民财产来帮助外国人。应该减少税收,提倡这个议题,并鼓励美国人创办和捐助那些从事相同工作的非政府组织。”
孟菲斯一所教会的一位牧师告诉我,必须“记得大多数福音派人士最初也认为艾滋病是性放纵的结果,尤其是同性恋的性放纵。所以我怀疑他们中有太多人仍然把艾滋病视为一种自招的瘟疫。我能想象那些道德主义者会说:‘这是他们自作自受。这是上帝对他们性罪恶的审判。他们不该指望我来为他们的药买单。’”
有些反对声音则根源不同。蒂姆·迪尔伯恩(Tim Dearborn)曾参与领导“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一个跨宗派的基督教人道主义救援、发展与倡导组织——正是在PEPFAR推出的那几年。他与世界宣明会、福音派全国协会、撒玛利亚的钱囊(Samaritan’s Purse)、其他一些基督教组织、摇滚明星波诺(Bono,2004年共同创办致力于对抗极端贫困和可预防疾病的“ONE运动”)、以及传教士华理克夫妇(瑞克与凯·沃伦是马鞍峰教会的创办人)一起努力,希望说服福音派群体关注艾滋病问题。
但世界宣明会也遭遇了阻力。“有人认为这要么是‘同性恋疾病’,要么是婚外性行为的结果,这种判断强化了福音派对该问题的抗拒与冷漠,”迪尔伯恩告诉我。尽管他们努力引导福音派将关注点放在非洲数百万人濒死的危机上,世界宣明会始终难以取得突破。“这从来不是福音派的优先议题,即使艾滋病的受害者中有很多是无辜的妇女和儿童,”他说。
肯·凯西(Ken Casey)在世界宣明会工作了二十多年,从2001年到2007年,他负责该组织对艾滋病疫情的全球响应。他指出了更深层的神学原因。“福音派倾向于强调人们一次性地决志信主,却往往忽略了耶稣命令我们要爱神、爱邻舍的教导,”他在邮件中告诉我。
福音派活出的是哪种福音?
因此,有许多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福音派群体没有对PEPFAR项目所面临的命运发出抗议,其中有些理由比其他的更容易理解。但有一个事实依然令人难以忽视:
白人福音派以压倒性的票数选出了这样一位总统——而正是这位总统,目前已经摧毁了一个被视为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公共卫生干预项目之一、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具人道精神的行动之一的计划。其结果可能是数百万人因此丧命。而一个自诩为“尊重生命”的宗教运动,多年来曾就堕胎、同性婚姻、色情、批判种族理论、女性参与战争、学校课程、体育博彩和赌博等问题高调表态,现在却几乎鸦雀无声。
一位保守派福音教会的牧师告诉我,他对此感到悲痛。“我被这种‘同情中的不作为’折磨得心力交瘁,”他说。“如果是一个民主党政府——冷酷地、非法地、完全没有必要地摧毁一个由福音派信徒祈祷、倡导、设计、甚至在许多情况下亲自实施的事业——我很难相信反应会比要求各州允许堕胎更不立即或更不强烈。”
他补充道:“对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欢欣破坏,对人命的漠视抛弃,以及随之而来的谎言,都是如此明显地越过了底线、严重违背了基督徒在世间应有的基本立场。若我们却将其视为普通政治事务,只是在欺骗我们的信徒,并削弱他们的力量——而当预测成为历史时,我们终将为不作为付出代价。”
富勒神学院前院长马克·拉伯顿(Mark Labberton)在其工作中发现,美国许多白人牧师如今看到的“底线”远远少于那些服务于有色人种社群的牧师们。
“白人教会和会众似乎对许多人正在经历的赤裸痛苦和苦难充耳不闻,”他说。“当我们的福音所处的社会位置让我们看不见、听不到、或不去关心那些脆弱者时,我们就已经背离了耶稣的道路。”他发问:我们究竟准备活出哪一种福音?
拉伯顿(Labberton)在20世纪70年代信主时意识到,这个信仰不应只是他人生的附属品,而是应当重塑一切的信仰。用《以西结书》的话来说,那种将石心换成肉心的愿景,似乎与福音派世界对PEPFAR终结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
对那些了解PEPFAR成就的人来说,这个项目理应是“拥护生命的基督徒”的显而易见的选择。获奖的基督教歌手兼词曲作者艾米·格兰特(Amy Grant)上月在田纳西州布伦特伍德(Brentwood)的一所教会,与其他福音派音乐人一起登台演出,以提升人们对PEPFAR的认识与支持。她说:“我看着保守派信仰群体,无数次听到‘拥护生命’这个词。我会想:‘哇!全球抗击艾滋病,简直是拥护生命行动中的巅峰。’”
她的发声得到了《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主编拉塞尔·摩尔(Russell Moore)的呼应。他告诉我:“PEPFAR对于福音派基督徒而言,本应是毫无疑问的支持对象。它体现了对人类尊严和生命神圣性的肯定,而且这正是我们国家有能力、也有责任去做的事情。眼睁睁看着一些人欣喜地摧毁这个美国福音派历史上最有效、最成功的道德改革之一——我们很难判断这背后到底是残酷的施虐欲,还是某种病态的自虐心理。”

2025年2月26日,示威者在国会山坎农众议员办公室大楼(Cannon House Office Building)外抗议。(Chip Somodevilla / Getty)
总统乔治·W·布什本人是一位基督徒,自称是“有同情心的保守派”。2003年,他曾表示,PEPFAR的道德基础是:“每个人都有价值,每个人都很重要,每个人都是全能的上帝所创造。”
几天前,在一段表彰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即将离任员工的视频中,他说得很直白:“2500万人原本会死,如今却活了下来——这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好事吗?我认为是的。”
福音派的文化滤镜
“我深切期盼福音派弟兄姐妹们能坐下来,认真看一看PEPFAR被关闭所带来的不成比例的数据影响。”——克里斯·戴维斯,那位来自格罗维顿浸信会的牧师对我说。“这项计划的成本只占联邦预算的极小部分,却已经挽救了超过2500万条生命。如果它被关闭,造成的死亡人数甚至可能超过美国每年因堕胎而失去的生命。如果我们只需用联邦预算的0.08%就能终结美国的堕胎死亡,福音派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支持。”
戴维斯对抛弃PEPFAR背后的冷酷感到悲痛:“这根本无助于解决国家债务问题,也没有把这些挽救生命的项目转移到其他资金来源上,却可能每年夺走数百万生命。”他说,“为的是什么?是哪门子的伟大事业?这正是我们在谴责堕胎时所表达的那种对生命的漠视。那我们为何对这种灾难性的生命流失却毫无愤怒?”
要回答这个令人刺痛的问题,就必须理解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塑造美国福音派的文化政治。
“人们头脑中戴着一副文化滤镜,而这副滤镜凌驾于福音派神学之上,”纽约市救赎主长老会(Redeemer Presbyterian Church)牧师迈克尔·凯勒(Michael Keller,教会创始人提姆·凯勒之子)告诉我。“福音派对PEPFAR的沉默,并不是神学问题,而是因为我们用这副文化的滤镜来决定如何参与公共议题。”问题在于,这种文化滤镜在太多时候与耶稣的优先关切毫无关系。许多以耶稣之名成为“文化斗士”的人,用“断章取义”的方式引用圣经来支持自己的政治观点。但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断章取义地使用圣经会将人引向极其危险的地方:圣经的经文曾被用来为灭绝、战争、反犹主义、奴隶制与种族隔离、地心说、甚至对进化论的攻击辩护。
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中,我们看到撒旦也曾引用圣经——《诗篇》第91篇——来试探耶稣,这或许就是“断章取义战争”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2014年,世界宣明会宣布将在美国雇佣处于同性婚姻中的基督徒。这一决定立刻引发了迅猛、猛烈且愤怒的反应。众多福音派领袖和组织谴责这家基督教人道主义机构背离了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
该慈善机构因此失去了超过3000名资助贫困儿童的捐助者,全国各地的福音派团体呼吁抵制。富兰克林·葛培理(Franklin Graham)和阿尔·莫勒(Al Mohler)等知名福音派人物公开抨击世界宣明会;莫勒称其决定是“一项严重且悲剧性的行为”。一些福音派学者更是斥之为“背叛”。世界宣明会那令人称道的人道主义工作似乎毫无分量——文化战争的斗争更为重要,即使无辜的儿童因此成为附带伤亡。仅仅两天后,世界宣明会就撤回了该决定。
这是一种发人深省的对比:一个受人尊敬的基督教救援机构决定雇佣处于同性关系中的基督徒,引发了整个福音派世界瞬间、愤怒而猛烈的反弹;而另一个几乎终结了在非洲拯救了超过2500万条生命的项目的决定,却几乎未激起任何波澜。即便是了解事态的人,也很少有人对此发声。而那些本愿意发声的人,也往往因惧怕后果而选择沉默。
由于川普政府赤裸裸的冷酷无情,我们可以预见:埃塞俄比亚将出现更多画有耶稣与死于艾滋病儿童的壁画;在马拉维等国家,将会出现更多“棺材街”;像约翰·罗伯特·恩戈尔那样被奇迹拯救的生命,将变得更加罕见。美国的福音派——出于种种原因——大多已经转过头去,对非洲大陆正在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他们还有别的事要忙,他们有文化战争要打。
耶稣在他那个时代也遇到过这样的人。他们是那些宗教领袖,当看到在去耶利哥的路上倒地呻吟的伤者时,选择了从另一侧绕行。(注)
【注:这是《路加福音》10:25-37,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耶稣回答一位精通犹太教教规的教师的质问:“谁才是我的邻舍?”(谁才是我该去关心的对象?)耶稣用比喻回答他,主要指明:你们看重的是字句上的教规,但这完全是本末倒置。没有了爱心,只会画地为牢的宗教是死的宗教。】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