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言:川普为何可能输掉对华贸易战
-
智者言:川普为何可能输掉对华贸易战
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我们对中国的看法存在严重错误
两位专栏作家探讨了川普和美国决策者在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中对中国的误解。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对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访谈
2025年4月15日编译:临风

【克莱因开场白】
我深信一个简单的原则:你无法为一个糟糕的政策提出一个好的论点。你也无法为一个前后矛盾的政策提出一套自洽的逻辑。
你可以想象出一些可以辩护的关税制度,也可以提出一些对过去全球贸易时代的合理批评。但问题在于,这些都无法套用于川普总统正在做的事情。
看着川普的支持者们在网上变换立场,简直令人苦笑不得:早上还在为关税辩护,说这是对一个被堕落和贪婪腐蚀的经济进行的必要“休克疗法”,还说我们只关心市场,而不是已经被遗弃的中西部地区;结果到了下午,又开始称赞川普暂停这些关税的决定是何等高明:看看股市的回暖,简直妙极了,先生。这就是《交易的艺术》的教科书式操作。
我写下这篇文章的时间是4月14日星期一。我们目前所处的状况,是与中国的全面贸易战。我们对全世界都加征了关税——但重头戏是中国。对中国的关税已经远远超过了百分之一百。
我们被告知,这一切都是必要的,因为我们需要把那些供应链从中国带回来,尤其是那些先进的产业链:中国建立经济和实力,靠的是我们的苹果手机、我们的电池、我们的半导体。我们需要把这一切都拿回来。
但不——等等,快讯:大多数电子产品现在被排除在中国关税之外了。我们这项旨在重塑先进制造业的政策,结果是对来自中国的鞋子征收比笔记本电脑更高的关税。苹果公司尤其似乎成功逃避了这些关税。
哦不,等等——也许不是。现在川普又说,他自己政府宣布的那些豁免是假新闻。那些商品稍后会以某种不同但无法解释的方式被征税。
甚至到现在,我也无法准确告诉你这些关税是什么、将会是什么。想象一下,企业要在这种政策下做出投资决策。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中国正在进行报复。他们已经暂停了稀土矿物和用于生产许多先进技术产品的磁石的出口。这样会有助于我们的制造商吗?他们连关键产品都无法生产,而中国却能?川普政府有没有对这种完全可预见的回应做出过计划?
这些问题本身就是答案。如果你和中国打起了贸易战,但最后输了怎么办?如果你惹怒了世界其他国家,也对他们征收了关税,但最终却让中国看起来更强大、更可靠、更有远见、更有战略眼光——在那些现在正在寻求摆脱美国霸权不稳定后果的国家眼中怎么办?
我今天想谈谈中国。我认为,政府之所以觉得退守到一个更像是与中国打贸易战的策略更安全,是因为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了一个关于中国的两党共识。这是川普在2016年竞选时点燃的火种,但后来民主党也加入了:中国正在崛起,而我们在让它崛起的过程中犯了严重错误。我们正面临衰落的危险。中国骗了我们。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制造业工作岗位。他们让我们和我们的盟友沉迷于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商品。而中国不仅仅想变得富有,它还想统治。先是台湾——然后谁知道会是哪里?
我不会告诉你这个故事完全是错的。不是的。而且我也不会告诉你,所有相信这一点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希望有川普的那场贸易战。他们没有。
但我会告诉你,多年来我对这个越来越鹰派、越来越愤怒的共识感到惊讶和担忧。质疑它变得如此困难。
当我意识到华盛顿已经选择了一个新的外交敌人,而且两党政治已经不再允许出现异见或不同理解时,我会感到紧张。所以我对对华政策的发展趋势早就感到担忧——并不是因为我认为中国是一个纯洁或良善的行为者,而是因为我认为政治已经围绕着敌意和升级形成了自我强化的结构。
我之所以担心,是因为我觉得美国的政策已经过时。它还想回到90年代或2000年代初。它关注的仍是过去的错误,而对现在的中国缺乏了解。
我听到一个人越来越大声地质疑这种共识,那就是我的《纽约时报》观点栏同事托马斯·L·弗里德曼。我在他最近一次访问中国后与他交谈,我记得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完了。我们搞错了。”
然后他解释了原因。
我觉得让所有人都听听他说的这些话是有意义的。不是因为大家都必须同意他的观点。而是因为,如果当前的共识政治正把我们带向川普所走的那条路,也许是时候听听那些质疑这一共识的声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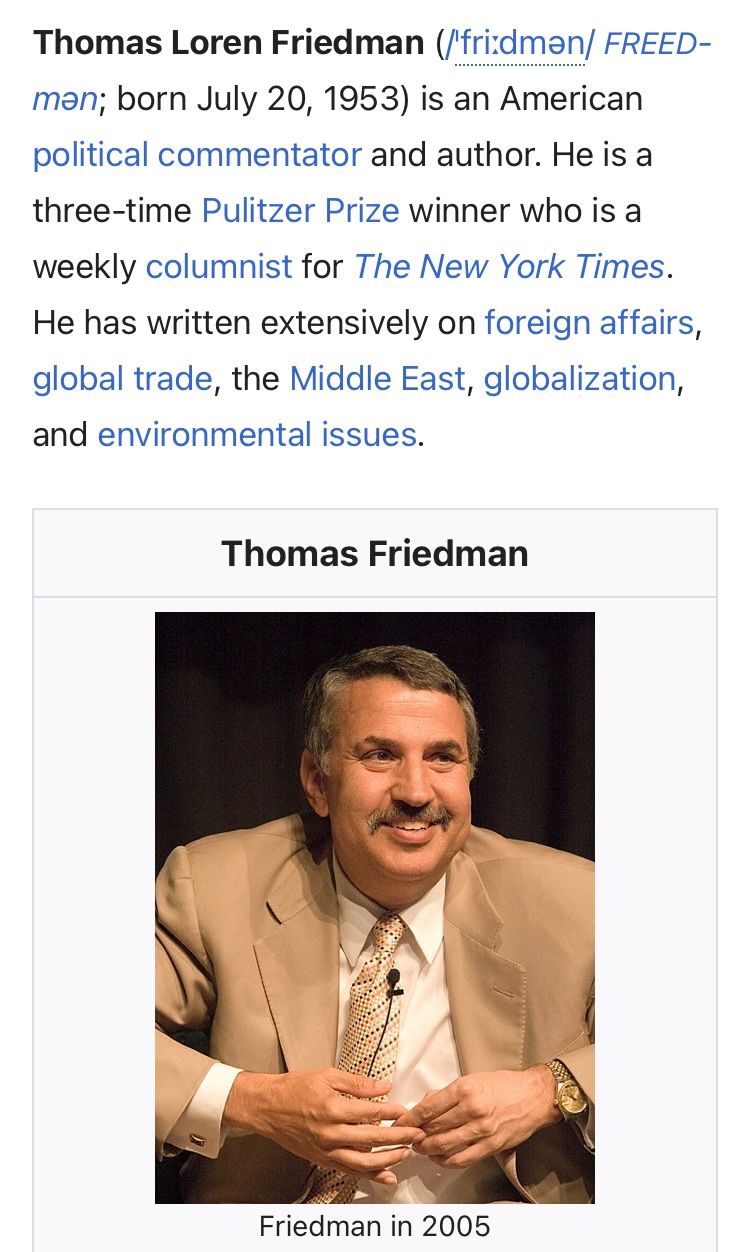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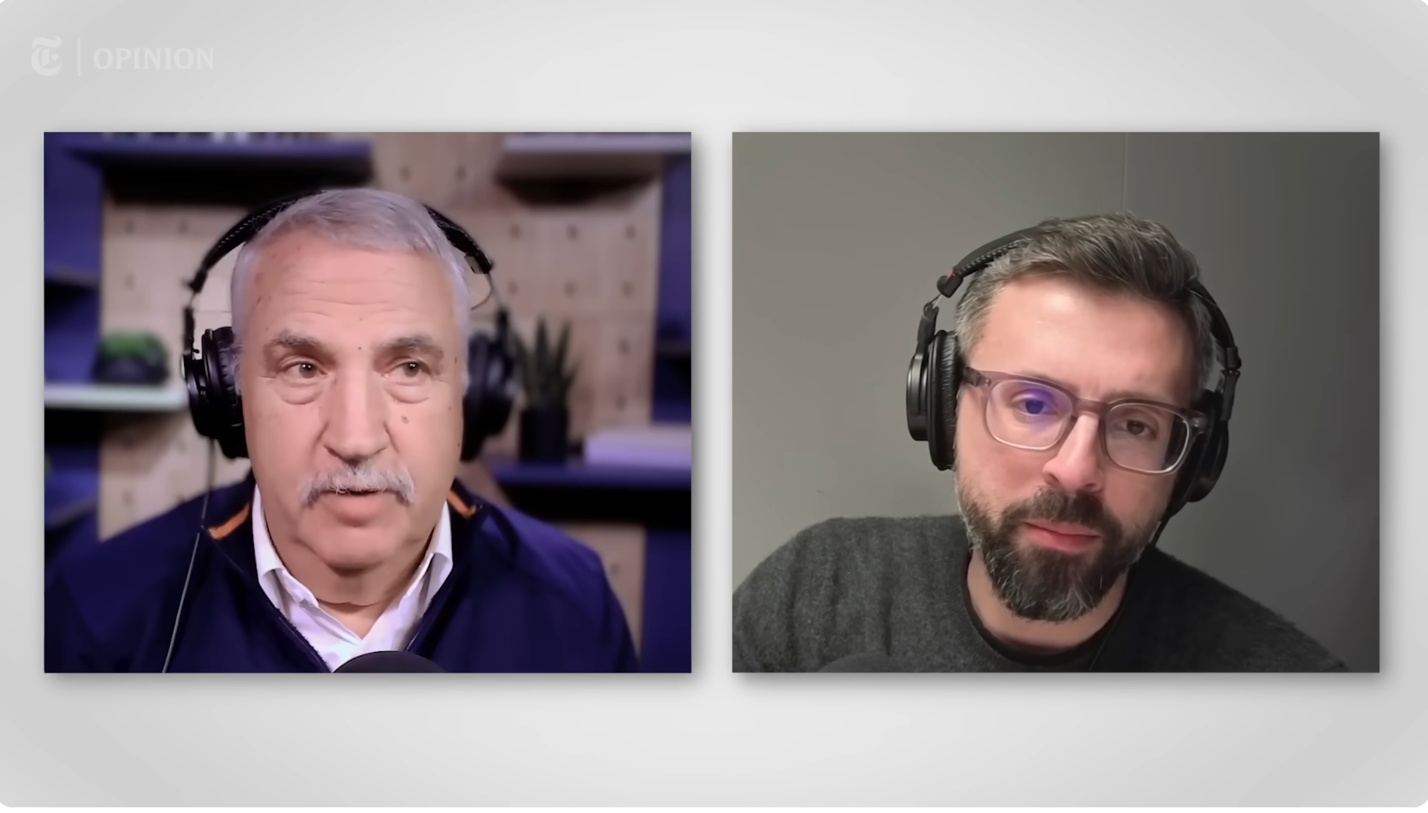
英文访谈链接:
【谈话记录】
埃兹拉·克莱因:汤姆·弗里德曼,欢迎你来节目。
托马斯·弗里德曼:很高兴和你一起,埃兹拉。
美国两党几乎唯一的共识
克莱因:你在最近的一篇专栏中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你说疫情对很多事情都造成了负面影响,但其中一个特别严重、却经常被低估的影响,是我们理解中国的能力。为什么这么说?
弗里德曼:疫情期间,几乎所有在中国的美国企业高管都离开了中国。然后在疫情过后,我们又开始“脱钩”的进程。所以你可以说,基本上有六年时间,美国人在那里几乎没有存在感。
我去年在中国的时候,感觉我好像是那里唯一的美国人。你真的见不到其他美国人——既没有游客,也没有商务人士,谁都没有。
我当时写道,中美两国就像两头大象通过一根吸管看对方。而就在两周前我再次前往中国后,现在我会说,它们像是通过一根针眼在看对方。这个“视口”变得极其狭窄。
克莱因:你曾提到,在那六年期间,美国国会只有一个代表团访问了中国。
你在专栏中也写过——通常在美国,政治问题的难题在于我们在各种议题上分歧太大,导致很难进行有逻辑的讨论。但在中国问题上,恰恰相反,我们达成了“过度一致”的共识。
你会如何描述华盛顿两党在中国问题上的共识?
弗里德曼:从川普第一任期开始,接着拜登政府,再到如今的“川普2.0”,在华盛顿基本上已经变得“违法”去说中国的任何好话。结果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去中国了。美国工业界开始回避雇用中国员工。美国大学也开始抗拒派学生去中国留学。
所以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不对称:中国每年有26万到27万学生在美国留学,而我们只有几千人去中国。
这背后的故事并不完全是美国的失败,也与习近平有关。他在2013年上台后,实际上让自己成为了“终身总统”。中国掉头而行,来了个大转弯。我们曾经以为中国是在“一步退两步进”地走向更多开放、更多与世界融合的轨迹,但这种趋势在习近平执政下戛然而止。
与此同时,他还启动了一个计划,旨在确保中国主导21世纪的所有关键产业,从航空航天到新材料、从自动驾驶到机器人。这完全改变了中美关系的化学反应。
而这个关系中的“压舱石”——埃兹拉——一直是美国的商界。从70年代末开始,是他们在中国赚钱。即便关系有摩擦,即便我们认为中国没有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下的贸易承诺,美国商界通常还是会游说政府说:“冷静点,没关系,我们在这里还在赚钱。”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一方面,习主席的“掉头转向”;另一方面,美国企业越来越觉得自己在中国得不到想要的利益,技术转让的代价太高;再加上中国本土科技力量的崛起——这三件事共同引爆了整个关系。
中国“健身房”
克莱因:你提到两国在科技、学生等领域的交流急剧减少。
而在美国这边,我也听到很多企业领导人和权力人士提到,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并认识到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工业、教育,甚至政治间谍活动。
关于中国学生在美留学、在美雇佣中国员工的担忧,很多是出于一种看法:尽管很难针对个人具体预测,但总体而言,这些都在助长间谍活动和技术机密的窃取。
而与此相关的,还有一种观点是: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厉害,而是靠“偷”。比如有一句来自共和党籍、在外交事务上有影响力的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的话:“中国不是在创新,只是在偷我们的技术。”

我很好奇你怎么看这种看法在整个局势中的作用?弗里德曼:我不能对间谍行为发表评论——我确实不知道其中细节。
在华盛顿,总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你知道我知道的,你就会更担心。”
而我对此的反应是:“我真希望我知道你知道的,这样我就能更全面地看待这个问题。”
但我内心的另一个反应是:希望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希望我们也在为国家安全进行情报搜集和间谍活动。至于“中国无法创新”这种说法——你只要跟在中国运营的美国或欧洲企业聊聊,就能发现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他们会告诉你:“我们最初是为了市场来这里的,现在我们是为了靠近创新而来。如果我们不在这里,就无法紧跟我们行业的前沿发展,特别是在汽车行业。”
中国意识到自己无法在内燃机领域与美国竞争,于是他们决定“弯道超车”,直接转向电动车,最终是自动驾驶。他们通过让智能手机公司转型成为汽车公司来实现这一目标。
疫情后我再去中国时,我简直惊呆了:我上次来时,小米还是个手机公司;这次来,小米已经变成汽车公司了。上次华为是手机公司,现在也是汽车公司。
他们基本上是把手机“装上了轮子”。而这很重要,因为你在中国坐“滴滴”(他们的“优步”),整个数字体验非常流畅,完全和你的手机同步。
我最近在中国坐了一辆华为汽车,车上还有一位华为员工。他拿出笔记本电脑,从车顶拉下一块屏幕,电脑立刻与屏幕同步,他就在车上办公。
他说:“你想看点什么吗?”
我说:“放保罗·西蒙在伦敦海德公园的演唱会吧,我在去你们园区的路上看看。”
我估计30秒不到就播放出来了。至于声音效果,埃兹拉——我从来没在一辆行驶中的车里听到过那种音响效果,简直遥遥领先于我在美国见过的一切。
我还见了大众汽车在中国的负责人。他们在那里建了一整套研发设施。他们称之为“为中国而在中国”——除非你和最强的竞争者一同训练,正如我的朋友、曾任欧盟商会中国分会主席的约尔格·乌特克所说:“除非你也进这个健身房,否则你会被碾压。”
克莱因:我们现在的这段对话,其实是源自我们一次有点随机的电话聊天。
你刚从中国回来,而我刚结束了一轮图书巡回活动。我们原本在聊别的事情,然后我问你这次去中国怎么样,你跟我说的是:“埃兹拉,你根本不知道我们有多惨。”
弗里德曼:是的,因为当你身在中国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他们三十年来不断“进健身房”的成果。过程是这样的:一个新产业出现了,比如太阳能板。中国的每一个主要城市都决定自己要有一个太阳能工厂。地方政府就会补贴它——可能是本地创办的,也可能是和外资合办的。
很快,你就会出现——我随便说个数吧——75家太阳能企业。然后他们彼此在这个“健身房”里疯狂竞争,最终剩下五家。这五家企业已经“健身健到极致”,于是他们就能以一种极具竞争力的价格和创新水平走向全球,让外国竞争者难以应对。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几乎控制了全球太阳能面板市场。
但你看不到的是,从最初的上百家企业淘汰到最终五家,这个过程中在国内也爆发出一整套庞大的供应链体系来支撑这个行业。
汽车也是这样,机器人也是一样。所以五年后,你会看到的是一个环环相扣的供应链系统。比如现在你是个中国年轻人,你说:“我刚有个点子,我想做一件衬衫,上面有个粉红色波点的纽扣,它还能倒着唱国歌。”——明天就会有人为你做出来。
克莱因:你描述的这个过程是这样的:中国政府认定太阳能是一个战略行业,然后通过各种手段,向全国这个产业注入大量的补贴性融资。
这也会产生一些很奇怪的情况。比如前几年有个例子,有一家陷入危机的大型房地产公司为了拿到融资,硬是去“转型”做电动车。
中国政府吸收了大量的浪费、失败,甚至腐败现象。比方说,“索林德拉”事件(Solyndra,美国一家失败的光伏公司),在中国这种事情可以乘以一千倍。他们容忍的事情,是我们在美国根本不可能接受的。
于是有很多公司只是白拿钱;有很多失败了;但在这些失败、浪费和腐败的背后,会诞生一些非常强大的所谓“国家冠军”企业。中国政府随后会向这些企业投入巨大的资源。
我还想补充一点,因为它关系到当前我们正在打的一些贸易战。中国之所以能有足够的资金搞这些事——不要求企业提高效率,也不要求投资更有效——部分原因就是他们压低国内工资。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出口远远大于内需。部分原因是他们维持一个结构极度失衡、以生产为核心的经济模式。
但回到你说的“健身房”这个概念:在美国,我们理解的资本主义是“适者生存”。而中国政府并不要求你一开始就很“健”,他们要求的是你最后必须“健”。
而我们则正好相反——除了少数风险投资例外,我们通常要求创业者一开始就得“健”。
弗里德曼:这是个非常好的观点,我来给你举个再合适不过的例子。
福特汽车目前在密歇根州马歇尔市建了一座电池工厂,使用的是拜登政府《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提供的资金。这座工厂是为电动车生产电池的。但技术却来自中国——是宁德时代(CATL)这家公司。这项CATL的技术,其实最早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诞生于美国。那时人们试图在美国本土规模化生产,结果失败了,破产了。
然后一位中国企业家收购了它,把它带回中国,在那里成功实现了规模化生产。现在,他们把这项技术转让给福特,技术又回到了美国。
这就是你说的“我们缺乏耐心”的一个完美写照。
华盛顿共识是怎么炼成的?
克莱因:我想回到“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这个问题上来。这其实也是我特别想和你展开这场对话的原因之一。
每当两党在某件事上过于一致时,我就会感到很不安。而现在,无论是在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中,你说过一句话:“你不能说中国一句好话。”
但我会这样表达:现在已经是一种彻底的全民共识,几乎成为政治上的“雷区”——如果你有任何全国性的政治抱负,你是绝对不能公开质疑“对中国强硬”是否是正确战略的,更别说主张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了。
你可以有川普那种版本的敌意:高得离谱的关税,充满敌意的措辞。
你也可以有一个更民主党式的敌意版本:比如拜登政府想要把一系列先进技术圈起来,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这可能是正确之举;又比如佩洛西访问台湾。
但你绝对不能持有这样的观点:对中国正确的策略是更多的互联互通,是努力把双边关系从战争边缘拉回来,避免双方不断升级敌意、不断为“全面冲突”做准备。
你一直在报道这个议题。你怎么看这个共识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是怎么从奥巴马时期、当时还在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那个策略是把贸易重心转向亚洲,同时也是一种较为温和的竞争方式——演变到现在,从川普1.0到拜登再到川普2.0,形成了我们几十年来最激烈的政策转向之一?
弗里德曼:让我从我自己的世界观说起,再回应你这个问题,我是怎么理解整个中美关系问题的。
我认为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时代——姑且叫它“后后冷战时代”——人类面临着三大生存性问题。
第一,是如何管理通用人工智能(AGI)。我们必须找到合作的方式,让它带来最大的正面影响,同时缓冲最糟的负面影响。因为这将是一个全新的“物种”。这是第一个挑战。
第二,是气候变化。我们现代发展的副产品已经引发了极为严重的气候危机,只有全球协作才能应对它。
第三,我相信这些压力的综合作用会导致很多“脆弱国家”崩溃,世界上将出现越来越多的“无序地带”。现在你其实已经能在一些地区看到这种迹象了。
在我看来,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能力应对这些挑战——前提是他们能展开合作:美国和中国。他们可以早点明白这个道理,也可以晚点明白。他们可以无痛地明白,也可以在代价惨重之后明白。但我的判断是:他们终究得明白这一点。
所以对我来说,“喜不喜欢中国”根本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我关注的,是我们将要进入的这个世界。
我还认为,这个世界将是一个新的“工业生态系统”。我出生的年代还是工业革命的尾巴,那时一个国家要想繁荣,就必须在煤炭、钢铁、铝、内燃机和电力这些领域里参与竞争。
但我们正要进入的这个新时代,其生态系统是:机器人、电池、人工智能、电动车和自动驾驶。这五个领域将成为经济的飞轮,推动一切。
因此,作为一个美国人,我的立场是:我们必须参与进这个生态系统,我们必须具备与中国在这些领域一对一竞争的能力。
我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整个中国问题的。我根本没在想台湾,也没在想什么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我之前还引用过一位川普政府官员的话,说“中国的目标是向世界传播威权马克思主义”。
天哪,埃兹拉,中国的目标有很多,但“传播威权马克思主义”绝对不在其中,好吗?
他们想传播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是“马斯克主义”——Muskism。他们的游戏目标,是在我们擅长的游戏中打败我们,而不是在卡尔·马克思的游戏里。
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一点,并严肃对待。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既然这些产业对国家未来至关重要——那我们就必须明白,这个国家:中国,不管你是爱也好,恨也好——我每天两个情绪都有。但他们是认真的。他们不是像你这几天看到的川普那样,在那儿瞎折腾。
他们通常不会任命一些傻瓜去做关键职位。他们不是在玩闹。
这就是我带着的所有“偏见”进入华盛顿这个辩论场的。结果我一走进去听到的就是:“你是‘熊猫拥抱者’吗?你是不是说了一句赞美中国的话?”
我只想捂着头发着火跑出去——因为那根本不是我们要面对的那个世界的讨论方式。
而我希望美国能在那个世界中真正繁荣。那个世界,需要我们拿出真正的认真态度。
克莱因:我想试着以最强的形式重构一下我认为华盛顿共识是如何形成的。
我和很多民主党人聊过这个问题,他们会说:汤姆·弗里德曼太天真了。当年我们买了一个大包装的“故事”,而这个包装里面有几个关键承诺。一个是:如果我们欢迎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他们会加大贸易、变得更富有、消费更多,而且也会逐渐自由化。
他们确实更富有了。但他们通过各种政策刻意压低国内消费,而且在习xx领导下变得更具威权色彩——你也提到了这一点,这对很多人来说是个大问题。他们还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比如对维吾尔人的打压。
但更深层的问题是,你对“中国共产党本质上是一个旨在扩张中国力量和传播其意识形态的项目”这一观点非常不以为然。
但他们会说: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真正深入了解习主席的治国方式,看看他强制官员学习的内容,这是一个极度意识形态化的扩张主义政权。
“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也越来越流行:世界上有两个超级大国,最终只能剩一个,我们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而我们至今所做的一切,其实是在削弱自己、增强中国。我们的工业基础已经过度转移到中国,我们对他们的供应依赖过大。
我觉得这一切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达到了高潮。人们看到欧洲因为依赖俄罗斯天然气而变得脆弱无比,也看到了全球对入侵的回应。这种时候,人们的感觉变成了:中国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危险得多。他们的工业基础是在牺牲我们自身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而他们并没有如承诺般成为一个“良性行为体”,无论是国内治理还是在国际体系中。
所以我们绝不能让自己处于一种未来与中国爆发战争或冲突、却还得指望他们来为我们生产对抗他们所需物资的局面。
因此,我们需要“脱钩”。我们需要认识到他们是一个对抗性强的国家,是一个需要像对待敌人一样处理的国家。
这就是我对“重心是如何转移”的理解。而我相信,我刚才讲的这些,很多国会中的民主党人都会同意——不仅是共和党人。
你觉得这里面错在哪?
弗里德曼:我只能代表我自己说话。我其实是支持川普第一轮关税的。事实上我还写过一篇专栏,标题大意是:“唐纳德·川普不是美国人应得的总统,但他是中国应得的总统。”
总得有人“吹哨喊停”。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对这个观点是有同情的。
还有一点我想在你节目上“忏悔”一下:无论我是在华盛顿写关于中国的文章,还是在中国写关于中国的文章,我其实写的都是美国。
我想用中国当作一个“永久版的斯普特尼克号”(指1957年苏联的卫星,激发美国科技和太空竞赛的象征)。让人们意识到,这台机器(中国)有多么强大——不管他们是怎么搞起来的——如果我们不认真起来,我们就会被他们碾压。
两件不可能同时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克莱因:我觉得在美国关于中国的讨论中,有一个非常扭曲的地方,是我们无法同时看到两件正在同时发生的事情。
一方面,拜登任期快结束的时候,主流观点是:中国的情况很糟糕。他们没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生活水平没有像人们预期那样显著提高。习近平的“清零”政策持续太久,极度威权。他们对科技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层面的严厉整顿让人觉得,他们自己在伤害自己的经济潜力。
人们当时真有一种感觉:美国比他们强,他们比我们弱。
但这中间漏掉了你在专栏里点出的那个关键点——我们想当然地以为,经济的复杂度(也就是它能制造出什么)和它为本国人民带来的生活水平,是紧密挂钩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如我们预想那样提升,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认知:中国的发展实验,其实并没那么成功。
但与此同时,如果你去看看他们在制造什么、看看他们的工厂和工业基础,他们在很多前沿科技上是领先的。在人工智能方面,他们与我们的时间差只有几个月——就算有这个差。你刚才提到,他们可能已经在电池、电动车这些领域走在我们前面。
弗里德曼:噢,这根本不在一个级别上。他们遥遥领先。
克莱因:而且在建设复杂供应链的能力方面,也更强。
我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看起来矛盾的现象,怎么能同时存在?
弗里德曼:这是我每次去中国都会问的问题,我这次也问了。
答案是一种混合体。部分是文化的原因,部分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理解他们的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并不是所有情况都这样,但大体而言:如果你在中国有一个创业的想法,其实不会有太多阻碍。政府不会来干扰你。事实上,他们可能比美国的地方政府、州政府甚至联邦政府还更积极地支持你。
但如果你想写一篇批评习主席的评论文章,那大概就是你人生中的最后一篇评论文章了。
这两者是分得很开的。而且,中国有很久远的“文官传统”。想进政府的人得考试,而且这个考试制度相当“功绩主义”。结果是——整体来说,中国的“深层国家机器”运作得还算不错,在支持创新方面很有响应力。当然了,它在你越界时把你抓起来这件事上也很有执行力。但这就是两者如何并存的方式。
所以如果埃兹拉你决定要做一个“粉红色波点唱反向国歌的按钮”——你不仅能在一夜之间把它做出来,而且没人会阻拦你。事实上你甚至能在本地找到不少资金来支持你生产这个按钮。
但如果你希望那个按钮反复播放“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那你就会被逮捕。
但这两种现实,在中国,就是并行存在的。
“黑灯工厂”与“华为新园区”所反映的现实
克莱因:我觉得人们已经习惯去想那个“有个按钮的粉红背包”,但他们不太习惯去想“黑灯工厂”或是华为的新园区。
什么是“黑灯工厂”?你走进那样的工厂是什么感觉?你去的那个华为园区又是怎样的?你从这次经历中带走了什么?
弗里德曼:“黑灯工厂”就是完全实现机器人自动化的工厂,所以它们是黑的——根本不需要开灯。除了凌晨两三点工程师来清洗机器时,才会开灯。而现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黑灯工厂。
至于那个华为园区——那是一个三年建成的园区,专门为三万五千名研究人员设计,包括他们希望招募的外国人才。园区里有一百家不同的咖啡馆,每幢建筑设计风格都不一样。还有一条单轨列车环绕着整个绿草如茵的校园。
顺便说一下,我去过深圳的华为总部。我对华为并没有幻想,我也写过相关的文章。他们确实偷过东西,绝对算不上“良好行为体”。但我们试图“干掉”华为——我们试图切断他们的芯片供应,他们一度几乎被打趴下。可他们又靠创新挺了过来。或许他们某个地方还是从英伟达那里偷来了芯片——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就在乔什·霍利(共和党参议员,密苏里州)公开宣称“中国做不出创新”的同一天,华为在 CNBC 上发布了创纪录的利润,而且是靠一些非常先进的新技术。
再次强调,我的工作是如实呈现世界的面貌。而现在这个世界的样子是:不管中国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他们确实已经到了。如果你还看不清这一点,那你就真的是看漏了什么重要的东西。
美国当前的荒谬现实
克莱因:这就带我们进入了当前的政策领域。
现在讲贸易政策真是太难了。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4月9日星期三,节目要等到下周二才播。鬼知道这六天之间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今天早上录,那节目可能又是另一回事了。
这几天全球市场暴跌,美债市场也开始动荡,结果川普政府开始退缩了,对那些没有报复美国的国家暂停征收关税,暂缓90天——这是一个挺怪的概念。但与此同时,他们反而加码了对中国的关税。
中国当然对我们展开了反击。川普政府的核心观点——由JD·万斯等人表达过——是:我们必须把制造业重新建回美国本土,不是建在盟友国家,而是建在我们自己这边。
拜登政府讲的是“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但商务部长霍华德·鲁特尼克谈到过他的愿景:方式就是征收非常高的关税——特别是对中国,当然,说实话,对世界其他国家也一样。因为你要实现的目标就是:把制造业全都带回本土。这是让我们重新具备与中国竞争能力的一种方式。
现在有一系列研究论文在提出这样的论点: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上已经处于霸权级别的主导地位。他们不是唯一的制造者,但他们是这个系统中的“老大”。而我们则掌握了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权。
根据这个理论,川普和他的团队正在试图把制造业从中国“夺回来”。
你觉得这个理论说得通吗?
弗里德曼:雇了小丑,就别惊讶你得到的是马戏团。
如果这真是你的理论,那你就去吧——第一天你可以把中国的关税调到一千个百分点,我没意见。
但这些人完全是“第一阶思维者”——只考虑第一步。
第二天你要做什么? 你早上醒来以后有什么战略?你如何在美国本土重建你想要的工业基础?你怎么利用你通过关税争取来的时间?
那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川普在中国面前竖起了一堵墙,然后他转头去把美国本土的汽车公司给“枪毙”了。
福特公司今天刚刚被降级了。我记得它的股价已经跌到七块五了。为什么?因为福特做了拜登政府希望它做的一切。一家理性的公司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希望它做的事情,它都做了。
然后,川普出现了,带着他那一套“右翼觉醒”的废话,说:“我们不要电动车。电动车是娘们开的,我们只搞男子汉产业。”
我只能说:去XX的。你看看现在福特的下场。
你说你要把制造业带回美国。很好,我支持。
但我不希望我孩子的未来是在车间里拧螺丝。我希望他们在设计、投资、发明下一代电动车。
再说回我之前讲的那个“创新生态系统”:电动车、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电池、清洁能源——这是一个整体。
但我在来这里之前还看到新闻说,川普想重开煤电厂。他热爱“钻油!钻到底!”("Drill, baby, drill")
那这一切就根本说不通了。
你要在中国面前建墙?好啊,我支持。但你墙后面到底在干嘛?你要怎么追赶?
现在你是在对准自己的公司、从背后开枪——只要它们不够“右翼觉醒”,你就整死它们。
川普政府现在专注的是什么?是看看能从美国大学砍掉多少研究资金,好“惩罚”他们搞多元、公平与包容(D.E.I.)的策略。
我要声明一下:我不是在为 D.E.I. 辩护。但如果我现在时间有限,我绝不会把精力花在这个上面。我会专注于加倍投资我们大学的研究能力,我会支持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加倍投入。
但他们在干嘛?他们在削减我们最顶尖科研机构的预算。
所以这一切,通通都是狗屁。
他们不是认真的人。
他们就是小丑。
人类共同体?
克莱因:但你并不完全支持“对中国筑墙”这套说法。你现在提出的观点,即使在民主党内部,我觉得都算是有点“异端”了。你在说的是:如果你是个认真的人,你应该像我们90年代对待日本那样对待中国。顺便一提,那正是川普形成他那一套贸易理论的年代。这人几十年来观点几乎没变过。
我们当年对日本的做法是:把他们的汽车公司引进来,然后我们向他们学习。而中国对我们的做法是:让我们把制造业带过去,他们向我们学习。
而你现在的意思是:如果你真的看清了中国在制造上的实力,那你就应该设法让他们的工厂进到我们这边来,以进入我们市场为交换条件,让我们也能向他们学习。
弗里德曼:没错!你应该跟小米搞50对50的合资企业。你们可以来美国造车,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是:你得把供应链也一起建在美国。不能只是在中国做完零件再运过来拼装,而是要在美国本土建完整的供应链和工厂——而且是合资的。这不就是你们当年对我们做的吗?
我以前就这么主张过,哪怕是对华为。华为确实有问题,他们的历史很复杂,卷入过各种知识产权的诉讼。
但我当时说:我会跟华为这样谈——“咱们来做个交易:你可以为怀俄明、蒙大拿和爱达荷这三个州铺设网络。你可以在这三州销售你的技术。我们会监控你三年,看看你怎么处理数据。如果表现良好,我们可以给你更多的州。”
但我们对华为做了什么?我们完全不给他们一个‘向上攀爬’的机会,没有任何激励机制,而是直接要“干掉”他们。
结果他们的反应是:“你跟我说话吗?你是在跟我说话?”
现在他们开始健身、锻炼、升级,可能要反过来把我们打趴下了。
说实话我现在已经搞不清我们对中国加了多少关税了——可能已经快无穷大了。但如果这些关税背后有一个严肃的战略,类似于我们当年“让他们进来、我们来学”的思路,那我举双手支持。
但如果战略只是筑一道墙,然后回去挖煤、靠石油生活、把风能和电动车产业一锅端,那这事的下场一定是场灾难。这是我们眼下面临的急迫问题。
而另一个大问题也在前方逼近——人工智能。
AI未来将被注入到一切事物中:从你的汽车、烤面包机、冰箱,甚至可能进入你的身体。如果我们和中国之间没有一个“可信架构”来管理 AI,那你家的一切都将变成下一个 TikTok。
现在我们为 TikTok 吵来吵去——我们能不能允许它?它是不是在监听我们?数据拿去干嘛了?这些问题未来都会适用于你的烤面包机、球鞋、汽车。这就是下一个问题。
克莱因:但那其实已经不是“未来”,那已经是“现在”了。他们不允许我们的科技公司进入他们市场,除了 TikTok,我们基本上也不允许他们的公司进入我们市场。
我一直说,AI 政策有三个目标:确保安全、加快进度、掌握主导权。
而“掌握主导权”总是那个最终获胜的目标。无论是拜登政府的讨论,还是川普政府的做法,都是这样。这也意味着我们对“确保安全”的推进速度被大大压缩,因为“速度”才变成了压倒一切的优先。
所以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赛道。而且你会看到两个 AI 体系被彻底割裂开来。其实两个互联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割裂了。
而这个世界的“割裂”,本身也挺有意思的。按照大多数说法,我们在 AI 上可能略微领先中国,但优势已经不大了。而中国有一样我们越来越缺乏的东西:一个全面数字化的经济架构,特别是他们把制造业、支付系统、通信体系都整合进了这个架构里,这意味着你可以非常快地将 AI 融入进这些系统。
马斯克说他想把推特打造成“万能应用”,其实他想的就是中国早就已经拥有的——一个集合通信、支付、社交、生活服务为一体的超级应用。而如果你把 AI 嵌入进去,就拥有了一个覆盖整个经济体的超级优化平台。
弗里德曼:对啊,我那篇专栏的主题就是这个: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数字化的社会。他们现在是“无现金社会”。你在街上看到的乞丐,都有一个二维码放在碗里。
我和《纽约时报》的同事基思·布拉德舍尔(Keith Bradsher)一起去了Zeekr,那是中国一家新兴的汽车公司。我们进入他们的设计实验室,看到设计师在做 3D 模型,把车置入不同场景中——沙漠、雨林、海滩、各种气候。
我们问他在用什么软件。我们以为是传统 CAD 之类的。他说:“不,是开源 AI 3D 设计工具。”
他告诉我们:以前这类设计他要做三个月,现在只需要三小时。
从三个月到三小时!因为他们有一个数字系统,可以让你把 AI 像针管一样直接注入,然后整个系统就自动优化起来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对“两个世界的分裂”感到担忧。我担心的是,这个分裂后的世界,不会稳定,也不会繁荣——至少远远不如过去四十年那样。
所以如果我能选择,我会继续主张——哪怕我是唯一一个主张这个的人:我们和中国必须坐下来,真正成为合作伙伴,一起设计这个世界的新架构。
否则,我们只会陷入一场疯狂的 AI 冷战,就像核竞赛一样,最终很可能两败俱伤。
这也回到我对未来世界的直觉:一旦我们进入 AGI(通用人工智能)时代,要想管理这个世界——不论是气候、AI,还是全球秩序的混乱,我们就必须作为同样一个物种,学会前所未有的合作。
我非常相信我朋友多夫·塞德曼(Dov Seidman)说的一句话:
“相互依存不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的现实。”
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要的是一种健康的相互依存,还是不健康的相互依存?
我们要么一起上升,要么一起沉沦。但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绑在一起的,宝贝。
这就是我的观点。克莱因:我不确定你说的是不是对的。你在国际关系和历史方面比我博学得多。但国家是可以各自兴衰的。超级大国会衰退,其他国家则崛起。日本曾经被认为是下一个强权国家,但现在它是一个正在老龄化、困境重重的社会。
我一直在思考的一种看法是,在川普政府将世界对美国的信任一把火烧光、却自称伟大的过程中浮现出的观念:中国的优势是制造业,而美国的优势,我们自己却在贬低,是金融。
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谁掌握金融,谁就掌握世界。川普政府自以为是在从中国手里“夺回制造业”。我不认为他们真能做到,但他们真正有可能做成的是让中国从我们手里抢走金融地位的一部分——因为人们将不再信任我们。
如果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刻、随心所欲地对别人加征关税,那他们就会主动地从我们的金融架构中“脱钩”。而这恰恰是美国权力的非凡来源。如果你滥用它,人们就会自动选择退出。因为,他们原本就是自愿加入的。
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支付结构,具备大量放贷能力。它现在正在努力塑造自己为一个更稳定的国际参与者,试图与欧洲、日本、韩国以及许多传统上关系紧张的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所以,我不觉得我们必然是“一起兴衰”的。如果你现在告诉我川普是一个“满洲候选人”(Manchurian candidate,间谍),而且你还有证据,那我真的很难反驳。你想啊,如果他真的是一个间谍,他还能做些什么比这更契合的呢?(笑)
弗里德曼:(笑)对吧?那我们回到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在贸易问题上认真的人,你会怎么做?
你首先要对中国说的是:你们现在制造了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产品。这根本不可持续。
你不能为所有人制造一切。你必须重新平衡你们的经济。在中国退休意味着一个月拿五美元的养老金。你们应该把一部分能量转向国内消费,多从别国进口。
谈判得从这里开始。中国生产太多,我们消费太多。
那为什么我们不让我们的盟友——欧盟、韩国、新加坡、日本、菲律宾——和中国一起坐下来?以“全世界对中国”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本可以对中国说:未来三年,我们将逐步提高关税,每年15%、20%、30%地上调。这样你们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们会作为一个联盟来推进。
然后,在那道“关税墙”背后,我们可以提供两个机会:第一,允许你们来美国投资。第二,我们自己也要真正重视制造业生态系统。我刚刚说过的那一套,我们要拿出激励措施,无论是对政府还是企业,全力推动基础设施和机会,为这个生态系统铺路。这才是理性的做法。
那川普做了什么?他变成了“美国对抗全世界”,是同时对抗全世界。所以他实际上把我们对抗中国的最大优势都给扔了——那就是我们有盟友,而中国只有藩属国。
川普制造的信任负债
克莱因:我想指出一点,这可能是思考贸易问题的一个有用方式。我觉得现在有个问题是,大家总是试图把川普的思路说得比实际更复杂。
弗里德曼:没错。
克莱因:就拿中美贸易来说吧。你前面说的对:中国大约生产了世界三分之一的商品。到2030年代,可能会达到45%。而他们的消费,占全球的比例,大概是12%左右吧?弗里德曼:对,12%、13%左右。
克莱因:这极度不平衡。一个那么大的国家,生产和消费之间有这么大的落差,会对整个全球系统造成不稳定。
川普贸易政策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点,甚至连很多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人也无法接受,就是他们试图把所有事情都看作是双边贸易问题,好像我们和越南的贸易账户也必须平衡一样。可我们搞的是高端制造业,越南要买我们什么?这完全是疯了的逻辑。
但你确实应该考虑“全球性的失衡”。不是说中国得少制造,而是他们得多消费。他们制造的产品应该有更多在本国被消费,而不是全部出口。这样全球才能维持稳定。
但如果你想要逼迫中国改革自己的经济结构,同时却激怒了所有其他国家……那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强权观念。如果你最担心的是中国成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那你可不能自己把自己变成更不具吸引力的选项。
弗里德曼:你得明白,我在来这的路上听说,川普又决定暂停加征关税了,莱索托(非洲一个小国)可以放心了。
川普不明白的是,世界——尤其是中国——已经把他看作是一个不稳定的行动者。他们看到我们现在发生的事。他们看到泽连斯基在白宫的那场会晤。看到川普撕毁了他自己刚刚与我们最亲密的邻国谈成的“新北美自贸协定”。他们现在在想两件事:
第一:我们的领导人要怎么跟这个人同场开会?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下一句会说什么。
第二:就算我们和他签了协议,他第二天可能就会撕毁。
他总觉得自己很聪明,好像自己在纽约长岛上买个公寓楼似的,可以随心所欲。但这可是真正的大事。别人不再认为他是一个稳定的谈判对手了。而这种出尔反尔,是有代价的。
我很高兴股市反弹了。但别以为这是“无成本”的。
克莱因:我对这件事感到非常愤怒。白宫新闻秘书对媒体说:“我猜你们很多人没读过《交易的艺术》。”
哦,天哪。当他宣布90天暂停时,根本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我们什么都没得到。是的,我们蒸发了大量财富。是的,我们释放了一个信号,让其他国家更少信任我们,并开始为这些90天后可能重新施加的关税做准备。
川普本人现在也变得不那么受欢迎了。我们给金融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们冻结了大量未来的投资。
这种认为自己装疯卖傻就能获得巨大让步的想法——我们根本没有获得任何让步。我猜他们的想法可能是:我们表现出很认真,所以别人会主动来找我们提出什么——比如越南可能会说要多买点我们的什么东西。
但我们什么都没得到。
我们所做的,就是把我们政治和地缘政治上的资本点了一把火。然后我们把这称作“胜利”。
但还有一点,现在川普也展示了他无法为所欲为。所以他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杠杆效应减弱了,因为世界刚刚明白:他实际上没法摧毁自己的债券市场。所以如果他再试图这么做,而世界又不想被我们牵着鼻子走,那他们可以选择“等一等”。
现在和中国之间确实有一个集中化的问题,我们会看看事态如何发展。但这次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弗里德曼:正如你所说,这比没有协议还糟。我们自残双足。现在我们在力量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因为我们疏远了所有本可以帮助我们联合对抗中国的盟友。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灾难。
“华盛顿共识”继续发酵
克莱因:我想再谈谈“华盛顿共识”。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川普,我觉得我们可以公平地说,我们都认为他的政策是愚蠢和具有破坏性的。
但这个共识的问题仍然存在。即便是今天,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很多人认为她将在2028年参选——也在发表演讲,基本上说:“我不认同川普的做法。但总体上说,关税是重要的。我们在本土生产得太少,在国外生产得太多。”
我和许多民主党人谈过,他们会说自己不认同川普的做法,但他关于中国的问题“大致是对的”。
而我担心的是,他们错了。他们正试图与15年前的中国竞争——那时候,也许你可以通过加关税来应对。
民主党人在中国问题上的本能反应是做“川普轻量版”。没有人真正为开放性做辩护。
即使你不相信这个主张,我认为也应该有人提出它,这样辩论才健康。除了你,几乎没人这样做。但同时,也没有人认为科技转移现在也许应该是反方向的。
我想最后让我感到担忧的是,这种关系有可能催生它原本要准备的事情。即使在拜登政府开始建立技术壁垒期间,我看到的大量报道都表明,我认为这是非常合理的,中国认为华盛顿此举是试图迫使中国放慢发展速度。美国永远不会允许中国在科技前沿取得进展——不管是不是扩张或敌对的意图。
而华盛顿内部的共识——认为中国必须被当作敌人来对待——本身就可能让中国变得更像一个敌人。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也不得不把我们当成更强的敌人来看待了。
我不是想替中国推卸责任。他们在这方面也做错了很多。但我担心我们正朝着一个充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世界一路狂奔——一个几乎注定充满敌意的未来,而两方都似乎完全没有兴趣去定义一条可能的“下车通道”。
弗里德曼:我想从两个方面回应你。我首先想回到我们之前讨论的“这个政府不严肃”的问题。
在川普宣布要对中国征收巨额关税的第二天早上,当市场大幅下跌时,我实际上打电话给我们编辑,说:“这不是今天最重要的新闻,也不是最令人不安的新闻。请不要忽视这个更大的新闻。”因为就在那天或前一天,我们得知——也可能只是据说——劳拉·卢默(Laura Loomer,一个阴谋论者,她相信911是美国自导自演的)竟然进入了椭圆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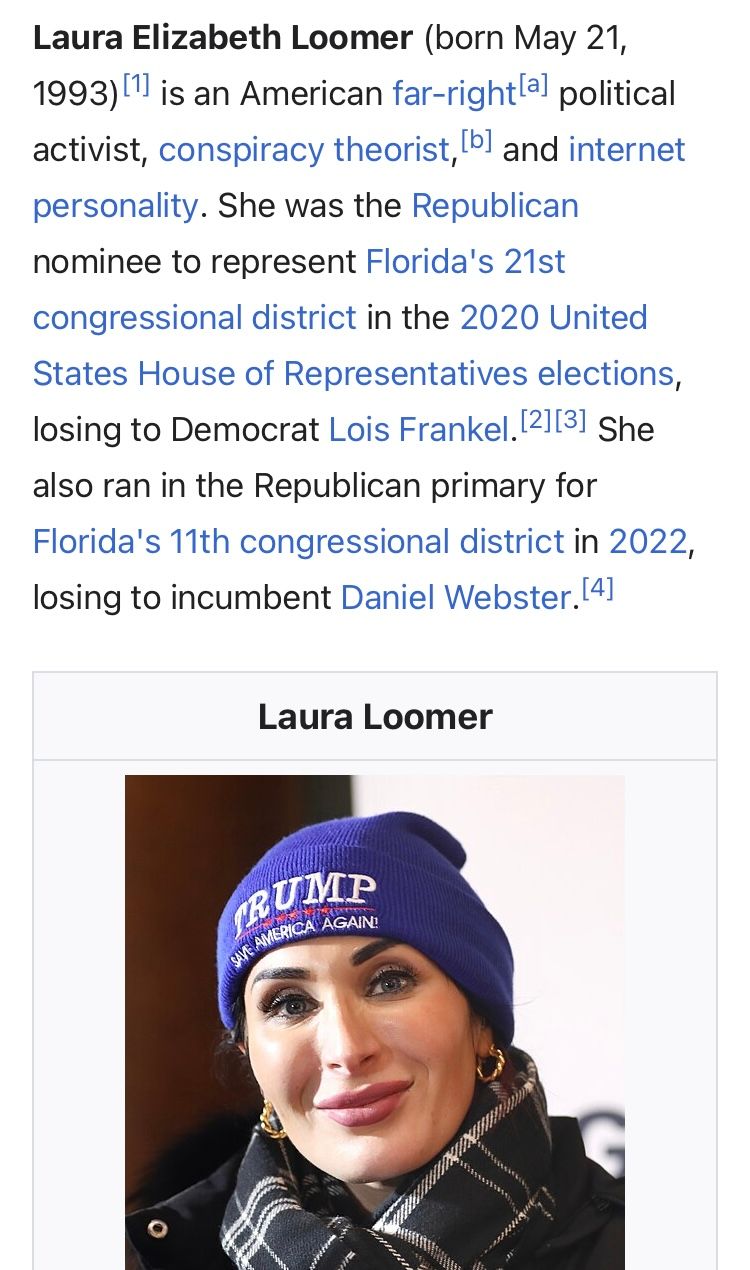
后来我们得知,她鼓动川普解雇我们国家安全局的局长和副局长——这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两位情报专业人士之一——因为他们不够“对川普忠诚”。谁知道具体情况如何?但川普真的照办了。
他就这样解雇了我们最重要的网络防御者和战争战略师之一——他们在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他是听从了一个“政治巫医”的建议才做的。
天呐,市场涨或跌都不重要。我们怎么还能自称是一个严肃的国家?这些事情会影响整个政府体系。还有人能向川普提供他不愿听的情报吗?
克莱因:我来做个有用的比较。
两年前,当外界开始下调对中国前景的传统看法时,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习xx开始羞辱、解雇,甚至似乎“让人消失”——像阿里巴巴的马云这样的高管——因为他们让他不高兴。外界当时的感觉是:中国在走下坡路。因为中国原本拥有的那种有效治理结构,能够吸收内部分歧,也希望看到其顶尖企业家和CEO成功,现在却正在崩塌成一个情绪化的独裁体制。
而现在马云又重新被接纳,习主席也在努力不再摧毁中国的科技产业,开始对包括马云在内的企业家发表温和的演讲。
而我们,却在做相反的事情。川普和马斯克正展开一场针对联邦政府的报复运动,打击惹怒他们的CEO、大学和民间组织成员。
我们现在似乎根本不在乎人是否胜任,不在乎他们是否取得了成就,是否是国家战略中的关键人物。我们正做着过去我们用来贬低中国前景的同样的事。中国已经掉头改变了路线。而我们才刚刚开始我们自己的“文化大革命”。
弗里德曼:我这次出访时,真的有很多人问我:“你们是不是在经历一场右翼‘觉醒派’版的毛式文化大革命?”
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什么?那是毛泽东发动他的意识形态青年,来摧毁中国的“深层政府”。结果并不好。这场运动持续了十年,天知道它让中国倒退了多少年。
所以我完全赞同你说的。这是我在观察这些现象时最感到不安的部分之一。
但我还想回到你说的另一个点。如果我参选总统,作为一个民主党人,我不会去做“川普轻量版”。
我会提出一个全面的替代方案:利用我们的盟友,设定条件——对中国征收长期关税,逐步实施;与此同时,在这些关税背后投资21世纪的生态系统,尽可能借助政府的帮助。要有长远眼光。因为我们是一步步陷进去的——我们不可能一步就跳出来。
牌局的目的?
克莱因:这其实引出了一个我很少听人问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的目标到底应该是什么?我们所有这些政策的目标是什么?
大多数时候,在一个默默受到“修昔底德陷阱”思想结构影响的对话中——也就是“天下只能有一个超级大国”的想法——政策的目标就是确保中国在财富、实力和影响力上永远不能超过我们。目标是要让我们自己保持领先,或是压制他们,而不是把我们的目标放在自身的强大和合作关系上。
我知道有人听到这里可能会说:你还真是天真,怎么可能谈合作?但欧洲的强大对我们并不是坏事。诺和诺德(Novo Nordisk)研发出一类卓越的GLP-1药物,这对我们并不是坏事。
老实说,我也希望能买到价格更便宜、性能更优秀的电动车。我从来没有真正支持拜登政府对电动车加征关税的做法。在我看来,他们选择与中国竞争的方式完全压倒了对电动车转型的推动,这就说明他们其实并不像说的那样真正关心碳中和的时间表。
我理解这些是困难的抉择,但它们确实反映出一个问题: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想要和另一个繁荣的超级大国建立一种关系?还是我们的目标是孤立中国,阻止它成为它本应成为的超级大国?因为我们认为共存根本不可能?
如果现在让人们坦诚说话,我认为华盛顿关于中美关系的讨论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几乎所有关键人物现在都相信后者。他们相信共存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就是一场全面的权力争夺战。而通用人工智能(AGI)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必须赢”的迫切,因为谁先取得突破,谁就拥有对方难以匹敌的巨大优势。
听起来你是在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前者。
弗里德曼:没错,目标应该是前者。我也乐意为这个目标做倡导者。
我们其实刚刚看到了一点点“另一个可能”的样子。而我认为,如果我们不改变轨道,我们会把自己搞垮。我认为我们会变得更不稳定、更不繁荣,也更无法应对21世纪的三大关键挑战——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的信任架构,以及全球秩序的紊乱。
所以,叫我天真也好,理想主义也罢,我都完全接受。只要别说我没做过功课——我做了。
克莱因:最后一个问题,我们也快结束了:你在过去一年去了中国两次,这都是相当重要的访问。你过去也去过很多次。在这些访问中,有什么是你听到之后最让你担忧的?有没有哪个会议、某个观察,让你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对于那些已经很久没去中国,或从未去过的人来说,我们到底忽略了什么?
弗里德曼:这次我和我们《纽约时报》的同事基思·布拉德舍尔一起去的,他已经在中国待了23年了。我们采访了两位教授,我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他们都非常亲美,专门研究美国。
其中一位告诉我们,他上次去美国,在登机口被带到一间小屋子里,应该是FBI的人,要求他交出手机。
另一个教授则是在抵达美国时被带走,进入小房间,也被要求交出手机。
如果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走,那真的很危险。因为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很快就会传开:“我上次去美国被FBI拉走了。”
然后其他人就会说:“我不想让我孩子去那儿留学,我不想去旅行,不想去旅游。”
我们会把自己变成一个“自我应验的预言”。中国人之间有个玩笑话,说整场战争其实是“我们中国人打他们的华人”的战争(有点民族主义的味道)。
亨利·基辛格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比如他在柬埔寨的轰炸政策。但我得说,他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现在非常怀念的人:他是一个理解美中关系重要性的共和党人。他的最后一本书讲的就是人工智能,是和克雷格·蒙迪(Craig Mundie)以及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合著的。可如今的共和党里,没有一个可信的权威人物可以让大家听进去。所以就变成了大家比赛谁能更猛烈地攻击中国。这种局面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埃兹拉,我要再强调一次:我去中国,是为了写美国的事。我试图拿出一面镜子,反照出一个对21世纪生态系统认真对待的样子,我这么做是为了我的孩子和孙子孙女。你可以叫我任何名字,我不会在意。
克莱因:汤姆·弗里德曼,非常感谢你。
弗里德曼:谢谢你,埃兹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