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党派的对话:范·琼斯与托马斯·L·弗里 德曼的对话
-
跨越党派的对话: 范·琼斯与托马斯·L·弗里 德曼的对话
编译:临风
2024年11月30日前言:
本访谈旨在藉着个人的故事,讲述如何与意见不同的人相处和了解。它帮助分裂的国家和人群意识到,我们是在同一艘船上的旅客,应当学习共存、共荣。CNN 明星记者兼政治评论员范·琼斯(Van Jones)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 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谈论琼斯如何与进步人士和川普政府合作, 确保一项重大刑事司法改革法案获得通过。了解他们如何成功应对激烈的政治分歧,以及为什么与不一定同意我们观点的人合作最终可能是推动我们国家前进的最 佳方式。该节目于 2024 年 10 月 6 日星期日在油管 Planet Word 频道上播出,作为“艰难对话”系列的一部分,旨在在两极分化加剧的时代促进建设性对话。在宜必思集团 (Ibis Group)的支持下,“艰难对话”系列旨在为与会者提供工具,让他们能够 尊重地参与关键问题的分歧。(本文的编译是 AI+人工的结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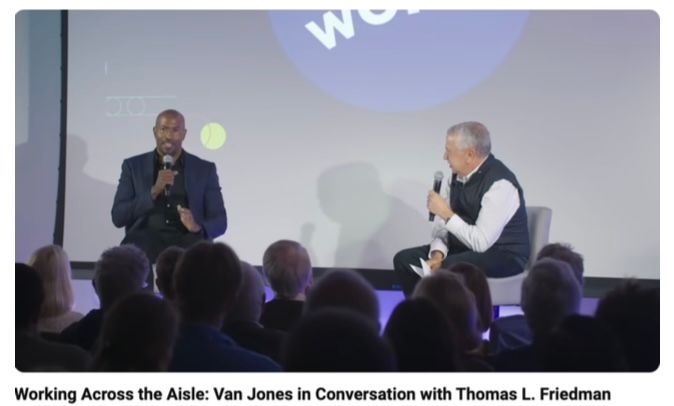
访谈:
托马斯·弗里德曼 (Friedman):
今晚能与我的朋友范·琼斯一起在这里,真是我的荣幸。信不信由你,范和我已经是老朋友了,我们的友谊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末。我想,也许我们可以从你告诉我 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开始。范·琼斯 (Jones):
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改变人生的时刻。我们那时在中国的大连,我是和一个青年代表团一起参加一个奖学金项目的。我当时一直在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工作,气候变化的讨论刚刚开始,你和戈尔以及其他人开始推动这个话题。我也在努力让低收入的非裔美国孩子参与到太阳能板安装的工作中,这成了我的热情所在,而且开始取得了些许成果。但这件事有点奇怪,而且在即使是在湾区,也偏离主流。于是,我站在中国一个长长的扶梯底部。这些扶梯的角度非常陡,持续时间也很长,而我正低着头,心不在焉地看着。我抬头一看,正从上面下来的竟然是托马 斯·弗里德曼。我心想,“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糟糕的时刻。”至少,如果你遇到你的偶像,你应该是在电梯里相遇,并且有一个电梯推销演讲,不是吗? 电梯演讲就像是在三到四层,五到六层楼之间,最多只有三十秒,最多也就一到三分钟的时间。
但这不是电梯,而是扶梯。根本行不通。这个人从这边飞快地下来了,我则从另一边飞快地上去,我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了。所以我心里想,我该怎么说呢? 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记者,他是那样的成功,而我只是奥克兰的一个无名小卒。当他走得越来越近时,我鼓起勇气说:“弗里德曼先生,我叫范·琼斯,我在奥克兰工作。我们相信绿色就业,而不是监狱。”还挺不错吧?他依然快速走过我,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那很好。”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下的楼,或者说是不是下去了,但我得到了他的联系方式。然 后,克林顿全球倡议会议在那之后不久就来了,你也去了。你同意和我坐下来聊一 聊,尽管那时有一百万个人想和你谈话,但你还是说:“我们远离这儿,去三条街 外的一个小咖啡馆。”我们坐下来,你拿出笔记本电脑,开始问我问题。我回答了你的问题,你说:“这个很有趣。有人写过这件事吗?” 我说:“没有,先生。”你说:“有人快写了。”三周后,你写了一篇关于我在奥克兰所做事情的专栏,开启了我在全国舞台上的职业生涯。这就是文字的力量。托马斯,感谢你。
托马斯·弗里德曼 (Friedman):
偶尔,我也能做对一件事。范,有一件事我们一直没有谈过——我很感兴趣,你一直是一个桥梁的建设者,但从不压抑自己的言辞。你不容忍愚弄,也不接受任何废话,但你仍然能够建立桥梁。能否谈一谈你是在哪儿长大的,这种推动力从哪里来,是什么让你培养出了这种能力,成为今天的你?范·琼斯 (Jones):
嗯,我觉得我可以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是威利·琼斯的儿子。这在华盛顿特区可能不算什么,但在我长大的田纳西州杰克逊市却意义重大。我的父亲 1944 年出生,生活在种族隔离和贫困中,他的家乡在孟菲斯的“橙色山”地区。我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南方,那是南方最大的黑人贫民区。我的父亲就出生在“枪榴弹屋” (shotgun shack)里。有些人可能知道什么是“枪榴弹屋”,如果不知道,简单说它就是那种房屋狭窄、 只有一间接一间的房间的结构,门口可以发射一个枪榴弹,穿透每个房间。那就是 我父亲成长的地方。为了摆脱贫困,我父亲在上世纪 60 年代加入了军队。每个人都想摆脱贫困,我父亲通过参军逃离贫困。然后他退伍,凭借退伍军人福利上了大学,进入了田纳西州的兰恩大学,那是一所黑人大学。他娶了大学校长的女儿,我的母亲,因为我父亲可是个了不起的人。我和我的妹妹是双胞胎。我父亲和母亲共同努力,把他的小弟弟——我的小叔——送进了大学,然后还送我的姨妈去上大学。基本上,我家每个人都因为我父亲的努力摆脱了贫困。当他去世时,他们在葬礼的程序单上放的是我毕业那天,我父亲站在耶鲁法学院前,举起双手的照片。那就是我的父亲。我这辈子一直在努力想:“我该如何赶上我的父亲?”他从一无所有开始,给我和我妹妹一切。而他去世后,街坊邻里都来了,因为他已经成了一个教育家,把一所失败的学校变得焕然一新,还得到了州的奖励。他的工作得到了广泛认可,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来告别。
我一直在想,我该如何做才能追上他。他唯一特别之处就是他能带领大家一起为孩子们做事。他是个很硬朗的人——他不太温和,握手的方式就像握住一块砖头。我记得我曾经告诉他,有一部电影叫做《Lean on Me》,讲述的是一位校长如何带领 一所学校逆转命运。他看了看我说:“你得靠自己!” 但他确实能把人聚集在一起,帮助孩子们。我看到了他在艰难的环境下如何做到这一点,尤其是在我们家乡实施种族隔离政策时,这对我影响很大。他从不做假话,做事非常直接,但他知道自己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帮助贫困孩子,而且他确实
把很多孩子从贫困中救了出来。托马斯·弗里德曼 (Friedman):
范,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我在你身上看到了这一点——那就是不仅要会说,还要会听。我自己也在写一本书,书名是《你听的时候说什么》。这是我在 70 年代报道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时学到的最大教训。我是一个来自明尼苏达的小犹太孩子, 当时我不想去那里说“你们都很好,都是其他人的错”。我不想去在人们面前这么说。我生存的法宝是做一个好的倾听者,当你认真倾听时,你能学到很多。一个方面是你学到了什么——因为所有我做错的故事都是因为我在应该倾听的时候却在说话。但更重要的是你说了什么。倾听是尊重的表现,如果人们觉得你尊重他们,他们会允许你说一些关于他们的事情。可是如果他们觉得你不尊重他们,你就连告诉他们天空是黑的都行不通。
这一点一直让我印象深刻,范。你真的是一个很有尊重的倾听者。这个特点是从你父亲那里学到的吗,还是你在过程中自己学会的?范·琼斯 (Jones):
我觉得如果你在一个小镇长大,你会在下一个周末在洗衣店、超市或者教堂见到同样的人。你根本没有空间对每个人都粗鲁。但如果你在大城市长大或者在沿海地区,社交媒体那些,你可以粗鲁一点而不必付出代价。对我来说,生存技能的一部分就是学会如何与人相处。我觉得南方人之所以在政治中往往做得好,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学会了如何与别人相处。我也觉得,长大过程中,你用的词并不多。所以,南方人有时就是这样:“你妈妈怎么样?”“我妈妈很好,你呢?”我们不会浪费太多时间在琐事上。但你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去听他们说话,这些东西会一直伴随着你。另外,我非常相信我们彼此需要对方。我为自己是个民主党人而自豪,但我知道, 如果我一个人掌权的话,我们可能会破产。我是那种会去喂养婴儿的人,但我不会 去问这是否在财政上可行。我需要一个保守派的人站在我旁边说,“那花费是多 少?谁来买单?”
我还特别想提到煤矿工人和黑肺病的问题。我一直认为,左派和右派都应该意识到,这个国家在煤矿问题上的两极分化给工人群体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煤矿工人,他们的工作直接导致了黑肺病,这是一种致命的职业病。我们不应该让这些人仅仅因为“生活在贫困中”就被遗忘。我们要记住这些工人,他们长期以来为国家提供了能源,贡献巨大,但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而那些在煤矿工作的人,很多时候他们只是为了生存,根本没有多少选择。虽然我们讨论绿色经济和环保问题,我们也不能忽视这群人的困境。很多煤矿工人现在正遭受疾病的困扰,他们的身体因为黑肺病正在遭到摧残。
而且问题是,煤矿工人甚至无法为自己发声,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呼吸。他们因为黑肺病而无法喘息。所以,我认为在讨论能源与未来时,我们必须讨论如何照顾那些为国家能源基础设施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人。这些人需要帮助,我们不能忽视他们在转向新的能源经济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这个问题不容忽视。我们必须想办法帮助这些人,确保在我们转向新的能源形式时,他们也能得到照顾。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只会继续撕裂这个国家。所以,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两边合作的另一个原因:确保没有人被落下,特别是那些在煤矿工作了一辈子、现在因黑肺病而死去的工人。两边的力量需要互相平衡。保守派的人需要像我这样的人,因为我会指出那些被忽视的群体。
托马斯·弗里德曼 (Friedman):
你知道,范,你的哲学一直给我印象深刻,它更像是一种“二者兼得”的哲学,而不是“非此即彼”。在我写的书中,我看到了美国的极化情况,从 1896 年到现在。 那张图显示了极化在 1896 年是很高的,然后在 1953 年明显下降,再然后又在现在急剧上升——形成一个大的“V”字型。我出生在 1953 年,明尼阿波利斯是一个非常温和的地方。看到政府起作用对我影响很大。这也让我倾向于... 我倾向于一种“二者兼得”的观点。我支持一个高墙和一个大门,我支持两个民族的两个国家。我支持市场推动的绿色经济。我也是中东和平的支持者,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我觉得你能从这里提炼出来,但你又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对我来说,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你与特朗普政府的工作——你曾经在监狱改革方面与他们进行对话。那必定是一场艰难的对话。请跟我们讲讲这个过程——它是如何开始的,如何演变的?
范·琼斯 (Jones):
嗯,开始时真的很糟糕。CNN 和特朗普政府之间发生了冲突。如你所知,我们并不合得来。事情开始于贾里德·库什纳,也就是特朗普的女婿,邀请我的老板杰 夫·扎克出门吃饭。他说这是华盛顿的新篇章。如果 CNN 想获得特朗普白宫的任何访问机会,他们必须证明他们能做到公平,而不是过于敌视特朗普。他说要证明这 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解雇安娜·纳瓦罗和我——因为我们对特朗普太严苛了。我觉得那非常不友好。那时候,我并不打算放过他。所以我那天晚上上节目时说: “贾里德·库什纳正在椭圆形办公室骑着三轮车,他该找份真正的工作了。”那并没有得到好评,所以我们并没有开始得很愉快。但这背后有一个原因。我与国家层面的保守派人士有过接触。我们曾一起参加一个 节目,并且讨论过刑事司法问题。商讨过广告后,他对我说:“范,你没有给我足够的压力。你一直在讲监禁行业有多种族主义,你没有看到保守派的角度。” 我问:“什么意思?”他说,作为一名财政保守派人士,他不能支持一个失败的政府官僚机构,它每年产生更糟糕的结果,但却能从中获益。并且他说:“我们党内有自由意志主义者,他们认为政府不应该在个人选择上过多干涉。你从来没提过这 一点。”
他还指出了一些我都不知道的事:比如共和党州已经在关闭监狱并改革系统,像德克萨斯州和乔治亚州。我甚至不知道这件事。于是,我意识到我们一直在互相误解。我一直在用正义的语言说话,而他则是用自由的语言。这时我就明白,我必须扩展自己的视野。刑事司法改革是有保守派立场的,并且它在特朗普身边得到了呼声。随后,贾里德·库什纳联系了我。我起初并不激动,但在思考过后,我意识到联邦监狱里有 20 万人,他们在未来四年、八年甚至十二年内根本没有任何人代表他们。我心想,“我真的是站在最弱势的人那边吗?”当贾里德打电话给我时,我意识到如果我不站出来,这些人将没有人代表他们。
托马斯·弗里德曼 (Friedman):
然后,结果如何?范·琼斯 (Jones):
我们和哈基姆·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以及其他一些人联手,最终推动了这项法案的通过。这并不容易。我们曾多次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但在最后的时刻,就在政府关门前,我们通过了这项法案。最终,这项法案使得 35,000 名犯人从联邦监狱中被释放。顺便说一下,通常来说,大约 70%的人最终会再犯并重新入狱,但由于我们改革的方式——我们一方面与左派妥协,一方面与右派沟通,并且达成了一些聪明的条款 ——实际上,并不是 70%的人再次犯罪。而是 15%——其中有一半是因为技术性违 规。这是史上最成功的监狱改革,由特朗普签署成法。他把笔递给我,那真的是一个胜利的时刻。真是令人惊讶的是,只要你让需要帮助的人先站出来,政治就不再那么复杂。托马斯·弗里德曼 (Friedman): 范,你在一个非常困难的对话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 10 月 7 日后。你 一直在进行一个很艰难的对话,涉及到黑人社区、犹太社区和穆斯林社区。谈谈这个问题吧。谈谈这场对话的挑战,因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对话。我知道得很清楚。你是如何进入这个话题的?你认为我们如何才能找到更好的前进之路?
范·琼斯 (Jones):
首先,我的教母多蒂·泽尔纳(Dottie Zellner)是 1964 年“自由夏季”运动中参加 南方行动的犹太人之一。那个夏天,她的三位朋友被谋杀——两位犹太人和一位黑 人。我小时候她对我影响很大,当我 20 多岁,在耶鲁法学院迷茫时,她成了我的庇护所。她当时在“宪法权利中心”工作,并带我去了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 地带,尽管哈马斯还没有接管。我还去了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特拉维夫、马达等地。
我对圣地非常熟悉,而她也教会了我很多关于黑人-犹太人联盟的重要性。我总是从她开始谈,因为她教会了我很多。她偏左,而我相较于她来说更为温和,但因为她,我明白了这个联盟的重要性。1909 年,美国的吉姆·克劳法(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恐怖主义的残酷程度,影 响了希特勒的思想。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实际上是受到了美国的启发。你必须理解,直到那时,尚未有一个从奴隶制国家变成了种族隔离国家。没有任何示范。而 黑人和犹太人联合创建了 NAACP
(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这就是一个黑犹联 盟,旨在推动废除种族隔离。这个联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 60 年代,黑人大学举手说:“把犹太的知识分子送来吧”,那时白人美国不再愿意接纳犹太人。黑人和犹太人长期合作,捍卫正义并修 复这个世界。但如今,我们看到了这种联盟的瓦解,这无疑是一个悲剧。和我的很多朋友不同, 我不担心犹太人,不担心黑人。我们在经历了 400 年的压迫后仍然活着,依旧在这里。真正让我担心的是,如果这两个群体——它们曾是推动美国民主创建和捍卫的 主要力量——开始彼此对立。若果真如此,民主本身将面临风险。托马斯·弗里德曼 (Friedman):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视角,范。我认为你表达了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如何从这里走出去呢? 我们如何修复这些正在增长的裂痕?范·琼斯 (Jones):
我认为它始于尊重。我们如何对话至关重要。人们可以一眼看出不尊重。人们可以在一公里外看出傲慢。我们使用的语言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说话时的“状态”。我们是从爱与尊重的角度出发,还是从评判与轻视的角度出发? 在进步左派的圈子里,有时有一个陷阱,那就是我们总是高智商、低情商——虽然
非常聪明,但却缺乏情感智慧。没人愿意被别人轻视。当我们谈论自己的观点时,我们往往是从“高人一等”的角度说话。我们经常陷入身份陷阱。身份确实很重要,但更关键的是:“你是不是喜欢我?”你能否看到我?我不单单是一个共和党人,民主党人,我不仅仅是一个共和党支持者。你能看到我,看到我是谁吗?我认为,修复分裂的最佳方式是创造一个让人们找到自己声音的空间。我曾经亲眼见到,当我跨越意识形态的舒适区,与我不同立场的人一起工作时,发生了很多积极的改变。我意识到你不必改变别人,你只需要创造一个条件,让他们自己找到前进的道路。我不是想改变那些煤矿工人,也不是想改变那些不同政治观点的人。我不是想让他们去支持民主党。我只是想向他们展示尊重与爱,并帮助他们看见我们有共同的目标。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坏人,问题在于太多的好人无法共事。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这不仅是政治的问题,它会带来文化和精神上的问题。如果我们让这些好人能够走到一起,那么我们就有办法解决社会问题。
托马斯·弗里德曼 (Friedman):
这真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问题,对吧? 你不能仅仅靠政治赢得这些战斗。你需要爱、尊重,以及寻找共同点的意愿。你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一直在展示这一点。范·琼斯 (Jones):
没错,爱与尊重是所有事情的基础。如果我们没有这个,那么其他任何事情都无从谈起。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爱是最强大的力量。”如果你爱一个人,他们就会倾听你。如果你不爱他们,他们将无法听你说话,不管你说什么。这并不是要赢,而是要搭建桥梁,找到帮助彼此看到对方的途径。托马斯·弗里德曼 (Friedman):
范,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我也希望给观众提供提问的机会。不过,在我们开始之 前,我想反思你之前说的一个问题。那时我们在电梯里相遇,我们开始了对绿色就业的探索,今天回头看,真是令人惊叹,我们从那个点开始。其实我有时并没有告 诉你,我在 2015 年把我的名片更改了,写上了“托马斯·L·弗里德曼,谦卑与尊严,专栏作家”。范·琼斯 (Jones):
(大笑)太棒了,汤姆,我喜欢这个。托马斯·弗里德曼 (Friedman):
但说真的,范,你在这个国家真是一个独特的声音——勇敢、真实,并且极具影响力。不过,我得问,你为什么不竞选总统呢?你确实有着将人们团结起来的天赋。你曾经想过从评论员的桌子后走出来,真正参与政治吗?范·琼斯 (Jones):
不,我从来没有想过。而且我会告诉你为什么。问题不在于政治,我认为我的职业对公众做出了巨大的误导。如果你整天都在看有线电视新闻,你会觉得美国有太多可怕的人。如果你天天看这些节目,你可能会觉得是共和党人太糟糕,或者民主党人太糟糕。但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问题不是坏人太多,而是好人太少,且他们不知道如何共同合作。如果你看新闻,你可能会觉得是因为有太多可怕的共和党人,或者有太多可怕的民主党人,或者有太多可怕的白人,或者有太多可怕的黑人。但事实是,问题不在于坏人,而是好人不知道如何合作。那才是问题。所以我不打算竞选总统。我的工作不是改变别人,而是让好人有机会做好。要是我 的工作能让 100 个人竞选公职,并做出有益的贡献,那比我自己竞选更有意义。这是我的看法。托马斯·弗里德曼 (Friedman):
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回答。你完全正确。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去改变别人,而是创造条件,让好人能够相互合作。政治不只是冲突,而是找到共同点,一起搭建解决问题的桥梁。范·琼斯 (Jones):
没错。你知道,我真心相信,如果我们创造这些条件,所需要的变化就会发生。我们必须让好人做好事的空间变得安全。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让世界变得更好。而这并不是单一党派或意识形态的成果,而是我们每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编辑:一民